爺爺的人生風景
一
在爺爺看來,吃苦是人生常態。
因為父母早逝,爺爺從小就跟著同處幼年的姐姐四處討飯度日。為了生存,他作出了人生第一個重大抉擇:拜師學藝,做篾匠。當時農村,篾匠、木匠、泥水匠雖不能大富大貴,生活還是比較有保障的。爺爺說:“學徒比要飯名聲好一點,跟做長工沒什麼區別,每天天不亮就得起來干活,師父稍不滿意,就粗粗一根鞭子抽過來。”
苦盡甘來,篾匠手藝徹底改變了爺爺的命運。新中國成立后,他成為了當地手聯社的正式員工,成了吃商品糧的公家人,后來還當上了竹器社的負責人。正是這一改變,使他能娶妻,置辦家業,有了一個完整的家。
起初沒有姑娘願意嫁給爺爺,也許是上天眷顧,奶奶剛好經歷了做童養媳的苦難,“真是被打怕了”,聽說爺爺沒爹沒娘,正納心意(客家話,合意願之意),以后再也不用擔心公婆打罵了。於是一對可憐的貧苦人,走到了一起相依為命。幾十年后,爺爺跟奶奶說笑,“那些人瞧不起我,不嫁給我,后悔了吧。”
爺爺的手藝,延續到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,成為了一項重要的收入來源。特別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,農業生產單元由集體轉為一家一戶,裝谷、晒谷用的籮、簟等竹制用具也從生產隊置辦轉為農戶自備。當時整個行政村隻有包括爺爺在內的三位篾匠,每年農忙時節,家家戶戶都爭搶著請他們去“打籮補簟”,不僅包伙食,每天還給1.2元的工錢,僅此一項農忙時即可收入約50元。爺爺說,這是一筆“大錢”。那時,大學畢業生一個月的工資也不過如此。
后來爺爺從手聯社調到搬運隊干了四年。搬運隊的主要工作,就是為基層糧管所把糧食從倉庫搬到外運車輛上,谷包每包重150斤,米包重200斤,全靠人力。所以搬運隊的員工大多為身強力壯的后生,而爺爺已是四十多歲的中年人,身高不到1.6米,體重不足90斤。搬運隊實行計件工資制,每搬一噸可獲0.4元。據說爺爺每月收入都有50多元,那意味著他每月至少搬運125噸谷米,平均每天搬運50多包。極難想象,一個如此瘦小單薄的男人,是什麼力量支撐著他,堅持了一千四百多個日日夜夜?
每每想起這些,我總是眼眶濕潤,汪然欲泣。
幸運的是,爺爺的身板一直很硬朗,直到老年,走起路來還是昂首挺胸。我想,一個人,隻要自己不低頭不彎腰,任何外力都是無法擊倒壓垮的。
我過繼到爺爺家生活后,口糧是個大問題。雖然生產隊安排了我的糧食供應指標,但也有村民風言風語說閑話:大人都在外面吃商品糧,沒有人在家務農,憑什麼要給小孩口糧?於是,爺爺奶奶商量,決定放棄工作,並於七十年代先后回到村裡務農。
爺爺奶奶說:“我們也有手有腳,就不信做不贏他們,養不起孫子。”
那時的農村,條件很差,收入很低。村裡像爺爺奶奶這樣的勞動力每天工分10分左右,分值在0.2元到0.4元之間,一年勞作,共約150元收入。爺爺奶奶的糧食標准是每人518斤稻谷,我大概400斤,按村民9.5元/100斤的配給價,全年收入也就隻夠買三個人的口糧,再怎麼節約,也省不了幾塊錢。包產到戶后,由於精耕細作、管理有方,我家糧食年產在3000斤左右,除了自己食用,尚有余糧近2000斤,當時的市場銷售價雖已漲到16.5元/100斤,滿打滿算也就值300多元。沒有經歷過農村生活、從事過農業生產的人很難體會農業之難、農民之苦,犁田、耙田、脫秧、蒔田、耘田、打藥、收割、綁杆、晒谷、作肥、看水、修田埂,早中晚三季,一季接一季,一年又一年,臉朝泥土背朝天,不知何日是終點。
“三農”問題,說到底,還是要種糧有錢賺,農業能致富。
鄉親們說,我們村因為人均耕地有1畝多,吃飯不成問題,關鍵是手頭沒錢,所以很多村民都想方設法搞副業。
爺爺奶奶也一樣,開荒種地,砍柴賣樹,種油茶,割鬆脂,在大隊部煮飯,隻要能增加收入,什麼都干。爺爺說:“有的事原來沒做過,不會做,也是逼上梁山。”
水到絕處是風景,人至絕境是重生。人生坎坷,唯有自渡。
后來爺爺接手了村裡的代銷店,這是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為保証農民基本生活供應而設立的。主要商品有煤油、食鹽、白糖、蘿卜干、霉豆腐、火柴等,價格全國統一,爺爺只是按營業額獲取3%~5%的手續費。由於本村人口少,人均供應量低,物品價格又很便宜,如煤油0.4元/斤、食鹽0.14元/斤、霉豆腐0.04元/塊、火柴0.02元/盒、水果糖0.1元/12顆,每個月的營業額在200元上下,手續費也就6元左右。現在我才恍然大悟,為什麼爺爺每次從鄉供銷社撥貨出來,都是自己翻山越嶺氣喘吁吁挑回家,原來每百斤有5元挑運費。爺爺說,我不像他們有力氣可以一次挑一百斤,但我可以多挑幾次。這點錢他實在舍不得讓別人賺。
一直以為爺爺開代銷店是他商品意識強,沒想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,是很多人都不願意賺這麼點辛苦錢。爺爺說,“天上不會掉紙票(客家話,鈔票之意),賺到一點是一點,一分是一分。”
正是爺爺奶奶這一分一厘的點滴積累,維持了我們整個家庭的運轉,並一直供我讀書直到大學畢業。
后來爺爺隨我到省城生活,他逢人便說,這輩子做夢都沒想到,一個“土古佬”(客家話,鄉下人之意)還能到城市生活這麼久,還能過上這麼好的日子,知足了。
二
容忍是爺爺重要的處世哲學。
在我很小的時候,爺爺就跟我講過他兄弟被害、被拐賣的故事。革命時期,尋烏是全紅縣,由於其地處贛閩粵三省交界的特殊地理位置,經常成為紅、白雙方反復較量、反復爭奪、反復征戰的地方。據爺爺回憶,他一位堂兄曾在外縣蘇維埃政府任職,一次回家探親被本地反動勢力謀害,一起被殺害的還有堂兄的父親。爺爺和他胞弟年幼在家,對方氣勢洶洶趕來,說“斬草要除根”。爺爺聽到動靜,當即帶著弟弟躲到村裡的石砌下水道裡。那下水道很長很深,蜿蜒曲折,連通各家各戶。爺爺就此躲過一劫,而他弟弟被抓,后被賣往外地,下落不明。爺爺曾多次要我去縣裡查查有沒有他堂兄的被害記錄,“也許可以評為烈士呢”。但因時間久遠,幾無線索。就這樣,爺爺帶著痛苦,帶著遺憾,把這些家事家仇,深深地埋在心裡。
一次大病之后,奶奶喪失了生育能力。那時候在農村,沒有子女、沒有后代,往往遭人歧視,矮人一等,抬不起頭來。“人多會恃勢,狗多會咬羊”。有的家庭仗著子女多,“拳頭大”,蠻不講理,以勢欺人。爺爺說:“痛腳趾越踩越前。”人越軟弱越受氣。一次,與鄰家爭執,對方惡語相向:“有什麼了不起,你家的筷子都沒有我家的卵多!”爺爺在世時從未跟我提起過此事,但我能體會,他在聽到這種極具侮辱和挑舋的語言后內心的痛苦和憤怒,這是一個男人尊嚴的底線、忍耐的極限。
羞辱是一把雙刃劍,有時可以擊垮一個人,也可以激發一個人。
“積谷防飢,養兒防老。”后來爺爺奶奶按照農村風俗嘗試過繼別人家的男孩為嗣,過程卻並不順利,一波三折。第一個對象是本鄉一個村民的小孩,隻住了幾個月就自己跑回去了。本來這在農村是很嚴肅的事,有人建議讓對方賠禮、賠償。爺爺說:“人都走了,算了吧。”后來他堂弟主動提出把自己的小兒子過繼給爺爺,爺爺很高興。為了讓繼子在村裡同伴之間有面子,上學時爺爺特意給他買了一個書包,買了一件價值三四十元的皮襖。這在當時的農村,是難以想象的奢侈。那個時候,有的家庭連5分錢一本的學生作業簿都買不起。正當爺爺傾情付出、對未來充滿期望之際,堂弟反悔了,一年之后,把兒子要了回去,沒有任何理由,沒有任何解釋。這對爺爺的打擊是巨大的。滿腔熱血被一盆冷水澆滅,美好願景被一記悶棍敲得粉碎。
兩年后,出於感恩,父親把我過繼給爺爺為孫。於是從滿月開始,我便在爺爺家生活,成了爺爺家幸福的一員。一切似乎又朝著美好的方向發展。
我因年幼,又無兄弟,在村裡常被欺凌,爺爺奶奶經常“打落牙齒肚裡吞”。一次,我與鄰家兩兄弟發生口角,對方一人拿著鐮刀、一人拿著磚頭追上門來,爺爺見后找他們家長理論,沒想到對方不但不制止,還破口大罵:“野兒雜種,難道你的小孩可以上金鑾殿?”屈辱、憤懣之下,爺爺把我捆綁在二樓的樓梯柱上,痛打一頓。老家有句古話,“人怕打,茅草怕扯”,可除了管住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,爺爺又能怎麼樣呢?回想起來,他也是用心良苦。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挨打,這一打,讓我刻骨銘心,終生不忘﹔這一打,打出了一個老老實實做人,從不惹是生非的孫子。
“謙謙君子,卑以自牧也。”忍辱負重,寬容退讓,是一種境界,一種修養,有時也是一種無奈,一種無助,可又何嘗不是一種自我保護,一種自守自強。
很多人和事都早已逝去,如微風吹過,不留下一絲痕跡。恃強、霸道、作威,都是曇花一現、過眼雲煙,終將成為他人茶余飯后的談資、笑柄。
對於我,爺爺是有所期待的。希望我能夠讀點書,有點文化,起碼有個高中文憑,“冇文化十分跌苦(客家話,沒出息之意)。”他經常比喻說,沒有文化的人就像田裡的泥蛇,沒本事﹔要學青竹蛇,本領大,能力強,“泥蛇一籮,不如青竹蛇一條”。
爺爺常給我講一些祖上的故事,念叨著化孫公、秋貴公、文壽公等一串名字。我對此毫無興趣,爺爺很是失望。后來,我通過有關資料了解到,張化孫是張姓始祖黃帝長子少昊第五子揮的嫡傳140世孫,宋中憲大夫,正四品,贛閩粵三省張氏客家人多奉他為始祖。爺爺當年常在我面前背誦的詩句,原來是張化孫的遺訓,即“外八句”:“清河系出源流長,卜處移居閩上杭。百忍家風思祖德,千秋金鑒慕宗坊。承先孝友垂今古,裕后詩書繼漢唐。二九苗裔能稟訓,支分富盛姓名香。”至於秋貴公、文壽公,原來是爺爺的高祖、曾祖,時為村裡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。爺爺說:“作水要跟水源頭。”無非是希冀我有出息,為家族長臉、爭光。
令爺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,常見於親生父母與養父母之間的矛盾和爭斗,在我讀高中特別是考取大學后也在我們兩個家庭之間不斷累積、爆發了,並且愈演愈烈。鄉親們說,那幾年,爺爺每每說到我,總是長嘆一口氣,“有沒有良心就看他自己了,由他心花開(客家話,隨他心願之意)。”甚至作好了我回到親生父母身邊、他自己孤獨終老一生的最壞准備。爺爺說:“他們這麼多人,搶都可以搶回去,我能有什麼辦法?總不能去尋死吧!”
1985年7月,我終於大學畢業參加工作,休假回到闊別一年半的家鄉,我的心情格外激動。到鄉裡那天,正值趕集。我打聽著爺爺是否也來了,這麼久沒見面,爺爺會是什麼樣子了呢?
順著鄉親指引的方向,我看見一個瘦弱老人正倚在一個小店的售貨櫃上,有氣無力地跟人說著什麼,凹陷得快要對穿的雙腮機械地抖動著,露出已掉去大半的殘牙。我的心一陣刺痛,這難道就是我日思夜想的爺爺?我顧不及多想,快步來到他身邊,哽咽著喊了一聲“爺爺”,爺爺沒有聽到似的毫無表情,毫無反應。是因為沒有事先告知爺爺太突然了,還是他一時激動不知說什麼好,抑或是久未回家而有些陌生甚至產生了猜疑、隔閡?也許兼而有之。
爺爺提議早點回家,我挑著爺爺的貨擔,走了一個多小時原來常走的山路,終於回到魂牽夢繞的小山村。爺爺在快到屋門口時要我駐足稍作停留,轉眼不知從哪裡拿出一盤似乎早已准備好的鞭炮,在竹竿上認認真真挂好並點燃后把我迎進了廳堂。我感到有些難為情,覺得他是不是太張揚了。可當我踏進家門,看著熟悉、簡陋的一切,我再也無法控制感情,眼淚奪眶而出。
為這一刻,爺爺已經等了很久了,這麼多年的辛酸苦辣,這麼多年的委曲求全,這麼多年的苦苦支撐,終於有了結果——自己養育出來的村裡第一個大學生回來了!那噼裡啪啦的鞭炮聲,是爺爺喜悅心情的美麗綻放,也是他壓抑內心的盡情釋放。
1992年,在愛人的支持下,我把爺爺奶奶接來身邊生活。此后幾年,家鄉不時傳來一些牢騷怪話:“牛耕田,馬食谷,別人生崽他享福。”聽到這些,爺爺已經不再在意,不再為此糾結、煩惱。
寒山問拾得:“世間謗我,欺我,辱我,笑我,輕我,賤我,騙我,如何處之乎?”拾得回答:“只是忍他,讓他,由他,避他,耐他,敬他,不要理他,再待幾年你且看他。”
三
鄉親們都說爺爺脾氣不好,過於“硬直”,說話做事“直棍鼓直窿,不會拐彎”。
村裡不少鄰裡糾紛家庭矛盾,一般人都是“頭顱縮進肚”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隻有爺爺會站出來“持公道”。因為輩分高,是村裡的“叔公王”,也不怕得罪人。
有件事我一直很困惑,為什麼爺爺沒有文化回到村裡后竟然做了三年出納?鄉親們告訴我,當時生產隊有兩戶人家比較強勢,誰都不服誰,誰都不放心對方,都防著對方,最后達成妥協,一致推舉了爺爺任出納。理由一是爺爺講原則,很硬氣,不會亂來﹔二是他剛從單位返鄉,家境比較好,不會佔小便宜﹔三是爺爺人單勢弱,好拿捏。
我曾問爺爺,做出納難嗎?他說:“事到臨頭就會了,關鍵是不能偏心,不能有私心。”其實爺爺也不是完全沒有文化,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他參加掃盲夜校學習,學會了不少字。有件事印象特別深刻,他的名字因為筆畫多,村裡人大多寫不出來,往往按諧音簡寫成“學林”,爺爺很不高興,幾次嚴肅地跟我說,他叫“鶴齡”,並一筆一畫地寫給我看。爺爺說:“寫字如做人,一定要認認真真,端端正正。”
大學期間和剛參加工作那幾年,我每次回家,都有很多鄉親自發來“閑談”,聊得最多的,除了國內外大事,就是基層的情況,特別是老百姓反映強烈的問題。如說基層干部作風不好,天天吃吃喝喝不做事,“中央都是好的,省裡也是好的,就是下面不行,基層干部帶歪樣”。還有說,農民稅收上交任務重,負擔不起。他們舉例說,農村養一頭豬不容易,一年大概能長到一百二三十斤,當時的肉價是1.1元左右/斤,除去自己吃的、“打發人情”的,也就賣個百把元,而稅收卻近二十元。如果算上飼養成本,要虧大本錢,農民怨聲很大。爺爺作為主人,總是一邊默默地做著遞煙倒茶的服務,一邊不時插上幾句話,“我就不信這些事沒人管!”
很多人都說爺爺平時“冇笑面”,喜歡“罵人”,不少人躲他怕他,敬而遠之,其實他是個熱心腸。
鄉親們有什麼困難找到他,他極少推脫,尤其對談婚論嫁生兒育女之事格外熱心,幾乎傾囊相助。有村民因為收入、長相等原因很自卑,不敢提親、相親,爺爺就鼓勵他們:“姻緣是配好了的,有曲棍子就有曲柴颯(柴颯,客家話,木柴之意),有駝背佬就有挺肚伯。”也許與爺爺的自身經歷有關,他總是說,“子女不怕多,有人有世界。”
爺爺最愛的,還是家人。尤其是對奶奶還有他的曾孫。他曾孫讀小學的幾年是爺爺最幸福的時光,每天一老一小手拉著手歡歡喜喜上學去,開開心心把家回。
對奶奶,爺爺傾注了一輩子真摯的感情。奶奶不能生育,爺爺從未提出過離婚。奶奶有次突發大出血,“起碼有一大臉盆”。那時村裡沒有通公路,爺爺硬是和人一起,用一張竹床抬著奶奶走了70多華裡趕到縣人民醫院,“撿了一條命回來”。奶奶說,爺爺一輩子沒有打過她、罵過她。“連大聲說話都沒有過。”奶奶說這話時臉上滿是幸福。
2004年,爺爺多次生病住院。經檢查,是嚴重支氣管疾病和尿毒症。住院治療的日子是痛苦的,也是爺爺無法忍受的。有一次他悄悄跟我說,如果哪天他實在受不了了,干脆就從醫院邊上的贛江堤上滾下去。我聽后極為震驚,也極為自責。我沒有跟他講更多的大道理,只是問他:“如果這樣做,別人會怎麼看你?又會怎麼說我?”他顯然聽明白了,此后一直表現得很堅強。
那天晚上,爺爺走得極突然。當我從單位匆匆趕回家,愛人告訴我,爺爺一直在等我,總在問:“怎麼就那麼忙啊?”沒有和爺爺說上最后一句話,是我一生的痛。爺爺對身后事唯一的交代就是:“要對奶奶好。”
奶奶后來健康活到93歲。
選自《星火》2024年第6期
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
- 評論
- 關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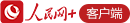




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
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
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
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
 關注人民網,傳播正能量
關注人民網,傳播正能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