爷爷的人生风景
一
在爷爷看来,吃苦是人生常态。
因为父母早逝,爷爷从小就跟着同处幼年的姐姐四处讨饭度日。为了生存,他作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抉择:拜师学艺,做篾匠。当时农村,篾匠、木匠、泥水匠虽不能大富大贵,生活还是比较有保障的。爷爷说:“学徒比要饭名声好一点,跟做长工没什么区别,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干活,师父稍不满意,就粗粗一根鞭子抽过来。”
苦尽甘来,篾匠手艺彻底改变了爷爷的命运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成为了当地手联社的正式员工,成了吃商品粮的公家人,后来还当上了竹器社的负责人。正是这一改变,使他能娶妻,置办家业,有了一个完整的家。
起初没有姑娘愿意嫁给爷爷,也许是上天眷顾,奶奶刚好经历了做童养媳的苦难,“真是被打怕了”,听说爷爷没爹没娘,正纳心意(客家话,合意愿之意),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公婆打骂了。于是一对可怜的贫苦人,走到了一起相依为命。几十年后,爷爷跟奶奶说笑,“那些人瞧不起我,不嫁给我,后悔了吧。”
爷爷的手艺,延续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,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。特别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农业生产单元由集体转为一家一户,装谷、晒谷用的箩、簟等竹制用具也从生产队置办转为农户自备。当时整个行政村只有包括爷爷在内的三位篾匠,每年农忙时节,家家户户都争抢着请他们去“打箩补簟”,不仅包伙食,每天还给1.2元的工钱,仅此一项农忙时即可收入约50元。爷爷说,这是一笔“大钱”。那时,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如此。
后来爷爷从手联社调到搬运队干了四年。搬运队的主要工作,就是为基层粮管所把粮食从仓库搬到外运车辆上,谷包每包重150斤,米包重200斤,全靠人力。所以搬运队的员工大多为身强力壮的后生,而爷爷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,身高不到1.6米,体重不足90斤。搬运队实行计件工资制,每搬一吨可获0.4元。据说爷爷每月收入都有50多元,那意味着他每月至少搬运125吨谷米,平均每天搬运50多包。极难想象,一个如此瘦小单薄的男人,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,坚持了一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?
每每想起这些,我总是眼眶湿润,汪然欲泣。
幸运的是,爷爷的身板一直很硬朗,直到老年,走起路来还是昂首挺胸。我想,一个人,只要自己不低头不弯腰,任何外力都是无法击倒压垮的。
我过继到爷爷家生活后,口粮是个大问题。虽然生产队安排了我的粮食供应指标,但也有村民风言风语说闲话:大人都在外面吃商品粮,没有人在家务农,凭什么要给小孩口粮?于是,爷爷奶奶商量,决定放弃工作,并于七十年代先后回到村里务农。
爷爷奶奶说:“我们也有手有脚,就不信做不赢他们,养不起孙子。”
那时的农村,条件很差,收入很低。村里像爷爷奶奶这样的劳动力每天工分10分左右,分值在0.2元到0.4元之间,一年劳作,共约150元收入。爷爷奶奶的粮食标准是每人518斤稻谷,我大概400斤,按村民9.5元/100斤的配给价,全年收入也就只够买三个人的口粮,再怎么节约,也省不了几块钱。包产到户后,由于精耕细作、管理有方,我家粮食年产在3000斤左右,除了自己食用,尚有余粮近2000斤,当时的市场销售价虽已涨到16.5元/100斤,满打满算也就值300多元。没有经历过农村生活、从事过农业生产的人很难体会农业之难、农民之苦,犁田、耙田、脱秧、莳田、耘田、打药、收割、绑杆、晒谷、作肥、看水、修田埂,早中晚三季,一季接一季,一年又一年,脸朝泥土背朝天,不知何日是终点。
“三农”问题,说到底,还是要种粮有钱赚,农业能致富。
乡亲们说,我们村因为人均耕地有1亩多,吃饭不成问题,关键是手头没钱,所以很多村民都想方设法搞副业。
爷爷奶奶也一样,开荒种地,砍柴卖树,种油茶,割松脂,在大队部煮饭,只要能增加收入,什么都干。爷爷说:“有的事原来没做过,不会做,也是逼上梁山。”
水到绝处是风景,人至绝境是重生。人生坎坷,唯有自渡。
后来爷爷接手了村里的代销店,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为保证农民基本生活供应而设立的。主要商品有煤油、食盐、白糖、萝卜干、霉豆腐、火柴等,价格全国统一,爷爷只是按营业额获取3%~5%的手续费。由于本村人口少,人均供应量低,物品价格又很便宜,如煤油0.4元/斤、食盐0.14元/斤、霉豆腐0.04元/块、火柴0.02元/盒、水果糖0.1元/12颗,每个月的营业额在200元上下,手续费也就6元左右。现在我才恍然大悟,为什么爷爷每次从乡供销社拨货出来,都是自己翻山越岭气喘吁吁挑回家,原来每百斤有5元挑运费。爷爷说,我不像他们有力气可以一次挑一百斤,但我可以多挑几次。这点钱他实在舍不得让别人赚。
一直以为爷爷开代销店是他商品意识强,没想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是很多人都不愿意赚这么点辛苦钱。爷爷说,“天上不会掉纸票(客家话,钞票之意),赚到一点是一点,一分是一分。”
正是爷爷奶奶这一分一厘的点滴积累,维持了我们整个家庭的运转,并一直供我读书直到大学毕业。
后来爷爷随我到省城生活,他逢人便说,这辈子做梦都没想到,一个“土古佬”(客家话,乡下人之意)还能到城市生活这么久,还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,知足了。
二
容忍是爷爷重要的处世哲学。
在我很小的时候,爷爷就跟我讲过他兄弟被害、被拐卖的故事。革命时期,寻乌是全红县,由于其地处赣闽粤三省交界的特殊地理位置,经常成为红、白双方反复较量、反复争夺、反复征战的地方。据爷爷回忆,他一位堂兄曾在外县苏维埃政府任职,一次回家探亲被本地反动势力谋害,一起被杀害的还有堂兄的父亲。爷爷和他胞弟年幼在家,对方气势汹汹赶来,说“斩草要除根”。爷爷听到动静,当即带着弟弟躲到村里的石砌下水道里。那下水道很长很深,蜿蜒曲折,连通各家各户。爷爷就此躲过一劫,而他弟弟被抓,后被卖往外地,下落不明。爷爷曾多次要我去县里查查有没有他堂兄的被害记录,“也许可以评为烈士呢”。但因时间久远,几无线索。就这样,爷爷带着痛苦,带着遗憾,把这些家事家仇,深深地埋在心里。
一次大病之后,奶奶丧失了生育能力。那时候在农村,没有子女、没有后代,往往遭人歧视,矮人一等,抬不起头来。“人多会恃势,狗多会咬羊”。有的家庭仗着子女多,“拳头大”,蛮不讲理,以势欺人。爷爷说:“痛脚趾越踩越前。”人越软弱越受气。一次,与邻家争执,对方恶语相向:“有什么了不起,你家的筷子都没有我家的卵多!”爷爷在世时从未跟我提起过此事,但我能体会,他在听到这种极具侮辱和挑衅的语言后内心的痛苦和愤怒,这是一个男人尊严的底线、忍耐的极限。
羞辱是一把双刃剑,有时可以击垮一个人,也可以激发一个人。
“积谷防饥,养儿防老。”后来爷爷奶奶按照农村风俗尝试过继别人家的男孩为嗣,过程却并不顺利,一波三折。第一个对象是本乡一个村民的小孩,只住了几个月就自己跑回去了。本来这在农村是很严肃的事,有人建议让对方赔礼、赔偿。爷爷说:“人都走了,算了吧。”后来他堂弟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小儿子过继给爷爷,爷爷很高兴。为了让继子在村里同伴之间有面子,上学时爷爷特意给他买了一个书包,买了一件价值三四十元的皮袄。这在当时的农村,是难以想象的奢侈。那个时候,有的家庭连5分钱一本的学生作业簿都买不起。正当爷爷倾情付出、对未来充满期望之际,堂弟反悔了,一年之后,把儿子要了回去,没有任何理由,没有任何解释。这对爷爷的打击是巨大的。满腔热血被一盆冷水浇灭,美好愿景被一记闷棍敲得粉碎。
两年后,出于感恩,父亲把我过继给爷爷为孙。于是从满月开始,我便在爷爷家生活,成了爷爷家幸福的一员。一切似乎又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。
我因年幼,又无兄弟,在村里常被欺凌,爷爷奶奶经常“打落牙齿肚里吞”。一次,我与邻家两兄弟发生口角,对方一人拿着镰刀、一人拿着砖头追上门来,爷爷见后找他们家长理论,没想到对方不但不制止,还破口大骂:“野儿杂种,难道你的小孩可以上金銮殿?”屈辱、愤懑之下,爷爷把我捆绑在二楼的楼梯柱上,痛打一顿。老家有句古话,“人怕打,茅草怕扯”,可除了管住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,爷爷又能怎么样呢?回想起来,他也是用心良苦。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挨打,这一打,让我刻骨铭心,终生不忘;这一打,打出了一个老老实实做人,从不惹是生非的孙子。
“谦谦君子,卑以自牧也。”忍辱负重,宽容退让,是一种境界,一种修养,有时也是一种无奈,一种无助,可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保护,一种自守自强。
很多人和事都早已逝去,如微风吹过,不留下一丝痕迹。恃强、霸道、作威,都是昙花一现、过眼云烟,终将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、笑柄。
对于我,爷爷是有所期待的。希望我能够读点书,有点文化,起码有个高中文凭,“冇文化十分跌苦(客家话,没出息之意)。”他经常比喻说,没有文化的人就像田里的泥蛇,没本事;要学青竹蛇,本领大,能力强,“泥蛇一箩,不如青竹蛇一条”。
爷爷常给我讲一些祖上的故事,念叨着化孙公、秋贵公、文寿公等一串名字。我对此毫无兴趣,爷爷很是失望。后来,我通过有关资料了解到,张化孙是张姓始祖黄帝长子少昊第五子挥的嫡传140世孙,宋中宪大夫,正四品,赣闽粤三省张氏客家人多奉他为始祖。爷爷当年常在我面前背诵的诗句,原来是张化孙的遗训,即“外八句”:“清河系出源流长,卜处移居闽上杭。百忍家风思祖德,千秋金鉴慕宗坊。承先孝友垂今古,裕后诗书继汉唐。二九苗裔能禀训,支分富盛姓名香。”至于秋贵公、文寿公,原来是爷爷的高祖、曾祖,时为村里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。爷爷说:“作水要跟水源头。”无非是希冀我有出息,为家族长脸、争光。
令爷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常见于亲生父母与养父母之间的矛盾和争斗,在我读高中特别是考取大学后也在我们两个家庭之间不断累积、爆发了,并且愈演愈烈。乡亲们说,那几年,爷爷每每说到我,总是长叹一口气,“有没有良心就看他自己了,由他心花开(客家话,随他心愿之意)。”甚至作好了我回到亲生父母身边、他自己孤独终老一生的最坏准备。爷爷说:“他们这么多人,抢都可以抢回去,我能有什么办法?总不能去寻死吧!”
1985年7月,我终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,休假回到阔别一年半的家乡,我的心情格外激动。到乡里那天,正值赶集。我打听着爷爷是否也来了,这么久没见面,爷爷会是什么样子了呢?
顺着乡亲指引的方向,我看见一个瘦弱老人正倚在一个小店的售货柜上,有气无力地跟人说着什么,凹陷得快要对穿的双腮机械地抖动着,露出已掉去大半的残牙。我的心一阵刺痛,这难道就是我日思夜想的爷爷?我顾不及多想,快步来到他身边,哽咽着喊了一声“爷爷”,爷爷没有听到似的毫无表情,毫无反应。是因为没有事先告知爷爷太突然了,还是他一时激动不知说什么好,抑或是久未回家而有些陌生甚至产生了猜疑、隔阂?也许兼而有之。
爷爷提议早点回家,我挑着爷爷的货担,走了一个多小时原来常走的山路,终于回到魂牵梦绕的小山村。爷爷在快到屋门口时要我驻足稍作停留,转眼不知从哪里拿出一盘似乎早已准备好的鞭炮,在竹竿上认认真真挂好并点燃后把我迎进了厅堂。我感到有些难为情,觉得他是不是太张扬了。可当我踏进家门,看着熟悉、简陋的一切,我再也无法控制感情,眼泪夺眶而出。
为这一刻,爷爷已经等了很久了,这么多年的辛酸苦辣,这么多年的委曲求全,这么多年的苦苦支撑,终于有了结果——自己养育出来的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回来了!那噼里啪啦的鞭炮声,是爷爷喜悦心情的美丽绽放,也是他压抑内心的尽情释放。
1992年,在爱人的支持下,我把爷爷奶奶接来身边生活。此后几年,家乡不时传来一些牢骚怪话:“牛耕田,马食谷,别人生崽他享福。”听到这些,爷爷已经不再在意,不再为此纠结、烦恼。
寒山问拾得:“世间谤我,欺我,辱我,笑我,轻我,贱我,骗我,如何处之乎?”拾得回答:“只是忍他,让他,由他,避他,耐他,敬他,不要理他,再待几年你且看他。”
三
乡亲们都说爷爷脾气不好,过于“硬直”,说话做事“直棍鼓直窿,不会拐弯”。
村里不少邻里纠纷家庭矛盾,一般人都是“头颅缩进肚”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只有爷爷会站出来“持公道”。因为辈分高,是村里的“叔公王”,也不怕得罪人。
有件事我一直很困惑,为什么爷爷没有文化回到村里后竟然做了三年出纳?乡亲们告诉我,当时生产队有两户人家比较强势,谁都不服谁,谁都不放心对方,都防着对方,最后达成妥协,一致推举了爷爷任出纳。理由一是爷爷讲原则,很硬气,不会乱来;二是他刚从单位返乡,家境比较好,不会占小便宜;三是爷爷人单势弱,好拿捏。
我曾问爷爷,做出纳难吗?他说:“事到临头就会了,关键是不能偏心,不能有私心。”其实爷爷也不是完全没有文化,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参加扫盲夜校学习,学会了不少字。有件事印象特别深刻,他的名字因为笔画多,村里人大多写不出来,往往按谐音简写成“学林”,爷爷很不高兴,几次严肃地跟我说,他叫“鹤龄”,并一笔一画地写给我看。爷爷说:“写字如做人,一定要认认真真,端端正正。”
大学期间和刚参加工作那几年,我每次回家,都有很多乡亲自发来“闲谈”,聊得最多的,除了国内外大事,就是基层的情况,特别是老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。如说基层干部作风不好,天天吃吃喝喝不做事,“中央都是好的,省里也是好的,就是下面不行,基层干部带歪样”。还有说,农民税收上交任务重,负担不起。他们举例说,农村养一头猪不容易,一年大概能长到一百二三十斤,当时的肉价是1.1元左右/斤,除去自己吃的、“打发人情”的,也就卖个百把元,而税收却近二十元。如果算上饲养成本,要亏大本钱,农民怨声很大。爷爷作为主人,总是一边默默地做着递烟倒茶的服务,一边不时插上几句话,“我就不信这些事没人管!”
很多人都说爷爷平时“冇笑面”,喜欢“骂人”,不少人躲他怕他,敬而远之,其实他是个热心肠。
乡亲们有什么困难找到他,他极少推脱,尤其对谈婚论嫁生儿育女之事格外热心,几乎倾囊相助。有村民因为收入、长相等原因很自卑,不敢提亲、相亲,爷爷就鼓励他们:“姻缘是配好了的,有曲棍子就有曲柴飒(柴飒,客家话,木柴之意),有驼背佬就有挺肚伯。”也许与爷爷的自身经历有关,他总是说,“子女不怕多,有人有世界。”
爷爷最爱的,还是家人。尤其是对奶奶还有他的曾孙。他曾孙读小学的几年是爷爷最幸福的时光,每天一老一小手拉着手欢欢喜喜上学去,开开心心把家回。
对奶奶,爷爷倾注了一辈子真挚的感情。奶奶不能生育,爷爷从未提出过离婚。奶奶有次突发大出血,“起码有一大脸盆”。那时村里没有通公路,爷爷硬是和人一起,用一张竹床抬着奶奶走了70多华里赶到县人民医院,“捡了一条命回来”。奶奶说,爷爷一辈子没有打过她、骂过她。“连大声说话都没有过。”奶奶说这话时脸上满是幸福。
2004年,爷爷多次生病住院。经检查,是严重支气管疾病和尿毒症。住院治疗的日子是痛苦的,也是爷爷无法忍受的。有一次他悄悄跟我说,如果哪天他实在受不了了,干脆就从医院边上的赣江堤上滚下去。我听后极为震惊,也极为自责。我没有跟他讲更多的大道理,只是问他:“如果这样做,别人会怎么看你?又会怎么说我?”他显然听明白了,此后一直表现得很坚强。
那天晚上,爷爷走得极突然。当我从单位匆匆赶回家,爱人告诉我,爷爷一直在等我,总在问:“怎么就那么忙啊?”没有和爷爷说上最后一句话,是我一生的痛。爷爷对身后事唯一的交代就是:“要对奶奶好。”
奶奶后来健康活到93岁。
选自《星火》2024年第6期
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
- 评论
- 关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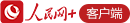




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
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
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
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
 关注人民网,传播正能量
关注人民网,传播正能量